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
十多年前,我從美國回到臺灣長住後,在華語世界裏努力提倡寫書評的風氣,並自願擔任某學術期刊的書評編輯多年,更喜讀《上海書評》,每週日一見,辦得有聲有色,為之鼓舞不已。書評之所以值得提倡,不僅因發達國家的期刊登載大量的書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書出之後有人讀、有人評,才有意義,學術才會因商榷而後有進步
書評的寫作有其基本規範,要評論一本書必須要先介紹一下書的內容,評論書中內容要針對議題,無論同意或不同意,不能不作說明,才能對作者與讀者有所交代。然而姚大力先生評拙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既不介紹全書的內容,又不認真對待書中提出可資商榷的議題,僅偶爾一提作者及其論點,他的基本心態是認為我們的“商榷”是無端的“攻擊”,應該虛心向“新清史”學習,完全不理會我們針對“新清史”所回避的問題,以及扭曲基本事實的缺失。他說“收入本書的八篇論文裏,只有一篇對‘新清史’有比較具體的正面肯定,還遭到主編者在‘導論’中的長篇批評”。這話是針對我而來,卻不敢明言,如何肯定、如何批評、批評是否有理,皆一概不論,這不是論學的態度。總的來說,姚先生長達兩萬餘字的書評,極大部分是借題發揮,並無新見,欲為“新清史”辯護代言而已。我們也歡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場、所思與所言。打個比方,律師要替被告辯護,總要瞭解被告的種種,才有可能打贏官司。要為“新清史”代言,至少要讀懂“新清史”作者群的原書。
姚先生認為漢化是“舊故事”,不值得再說,這可不是“新清史”作者們的認知。他們面對“漢化”如臨大敵,因為不僅中國學者有此說,而且許多著名的西方學者也持此說。所以他們認為那是必須要批判的“大議題”,要糾正的“錯誤故事”。例不細舉,便知他們是不認同“漢化”的用詞與概念的。請看歐立德 (Mark Elliot)說:“儘管滿洲的同質化有許多不同層次的象徵,必須說:用‘漢化’一詞來描述此一過程,是相當錯誤的。”(Despite the many and varied signs of Manchu acculturatio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using the word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is rather misleading.)(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p. 28)克勞絲蕾(Pamela K. Crossley)女士拒絕漢化之說最烈,她痛斥此詞“觀念不清,思維乏力,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上沒有價值”[見她所作“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文,載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p.2]。她又說:“繼續不斷地用此詞(漢化)模糊了清朝許多政治與文化發展方面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勢必有將中國認同束縛於二十世紀早期極其誇大矯飾的民族主義之虞”(The persisting use the term has obscured man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ore important, threatened to shackle Chinese identity to the rigid conceits of nationalist rhetor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223-24)。克勞絲蕾漢名柯嬌燕,我認識她,知道她早已放棄這個漢名,很不願意再聽到它;她連漢名都不要了,可略見她厭惡漢化之甚。姚先生認為她不是“堅定的反漢化論者”,既不知其人,也未讀懂其書。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最後的皇帝們:清帝國制度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更引用柯嬌燕之說,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漢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是清朝終結之後,於1912年在討論國家定位時才出現的 (見羅書第2頁)。足見這幾位“新清史”健將是不認同“漢化”這個名詞與概念的,大有去之而後快的意思。姚先生認為“漢化”是被新清史所接受的結論,是嚴重的誤讀與曲解。
姚先生認為“羅友枝發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像清代:清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標誌著‘新清史’在學術界現身的一個綱領性檔”,也是無知亂道。其實,羅文引用了許多新清史的觀點,有很長的書目。羅女士發難抨擊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在著名的《亞洲研究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的《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卻粗心地將此文誤作何先生于1975年當選為亞洲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說辭,更不當地從何先生所論清代的五項重要性中僅抽取“漢化”一項而加以抨擊。何先生論文所舉的五項重要性,“漢化”僅是其中的第三項。列為第一項的就是滿族統治者在二百年間開創了“一個最龐大穩固而行之有效的多民族帝國”(the largest consolidated and administratively viable multiethnic empire),認為是綿長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貢獻”(a unique contribution)(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 123)。羅女士單挑“漢化”,足見她並不如姚先生所認為的,漢化是可以接受的老故事,而是急切需要針對的重要故事。否則,何先生何須以“維護漢化”來回駁?遺憾的是,姚先生未細讀兩位的原文,貿然為羅友枝女士撐腰,矛頭指向何炳棣先生,認為何先生是一極端的漢化論者。
姚先生甚至認為他比何先生更能讀懂羅女士的原文,未免過於自信,甚至扭曲事實說,羅女士“對何炳棣偏執於一種視角的立場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確的批評”,若真正讀了何先生的文章,能說“何炳棣偏執於一種視角的立場”嗎?在此不妨略說我所知的內情,何先生有力的駁文,被期刊編者當作正式的論文在《亞洲研究學報》上發表(Feb., 1998, pp. 123-55),不料羅女士雖經編者一再催促,終未能回答。羅女士挑起筆戰,卻又拒絕應戰,在有理必須說清楚的西方學界,實不多見。何先生曾對我笑稱:“大水豈能沖倒龍王廟!” 沒想到,十餘年後,他的祖國居然有人認為“大水沖倒了龍王廟”,若他尚健在,必會大發雷霆。
按大清帝國的疆域涵蓋內亞,沒有錯,“清王朝代表了內亞和東亞相統一的最高階段”,或“清的統治模式是內亞和東亞的統一”,也沒有錯。既沒有人“只見內亞、不見東亞”,也沒有人“只見東亞,不見內亞”,問題是中心在東亞還是內亞?姚先生似乎是認同“新清史”所說,元和清是兩個內亞邊疆帝國,那帝國的中心在內亞了?所以他相信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說是“元、清在創制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實則萌芽於遼,發育于金,定型於元,而成熟、發達於清”,又說清帝“心目中,漢、唐、宋、明是一種一統,元、清又是另一種一統”。這是附和“新清史”的主張,滿清帝國是屬於滿族的內亞帝國,有異于中華帝國,所代表的是“大滿洲風”(pax Manjurica)而非“大中國風”(pax Sinica)。中國歷史上居然有“兩國論”,符合歷史事實嗎?滿清入主中原後所締造的內亞帝國乃中原之延伸,中原與內亞既非對等的實體,也非可以分隔的兩區,而是一個大一統帝國。雍正皇帝正式批駁華、夷之分,中外之別,“尊崇孔子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姚先生居然把雍正帝所言“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說成清僅繼元之一統。雍正明明是說合兩者的大一統為一。乾隆皇帝更以中國歷史為己任,修成《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將“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視清朝為四千餘年中國歷史的承上啟下者,中華史學傳統之執行者,以大一統為中國正統之繼承者,並強調大一統政權就是“為中華之主”。清代重修的遼金元三朝歷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乾隆所謂“海寓同文”,何來不一樣的大一統?包含漢族以及許多其他族群的“大中國”,正是包含何炳棣在內的我們,視為當然之事,“新清史”能接受嗎?顯然不能。他們明言要以“大滿洲”取代“大中國”,他們眼裏只有“大滿洲”內的“小中國”。
“新清史”的“內亞視角”固然有其價值,有助於認識多元中國,但不能說有了內亞,中原就成為內亞的附屬,邊緣成為中央,中央反成為邊緣,說得通嗎?元、清兩代的蒙古族、滿族皇帝入主中原,都想當中國的皇帝,建都于北京,顯然主要立足于中原視角,而非內亞視角。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領土擴充到全球,雖號稱日不落國,但仍然是大英帝國,號令發自倫敦,中心仍然是英倫三島而非印度或澳洲,並未因“世界視角”而改變了大英帝國的本質。美國立國時不過十三州,不斷西進後才抵達太平洋海岸,比最初的領土增加了三分之二,後來又併吞了夏威夷與菲律賓,但首都一直在東岸的華盛頓,並未因西進而改變美國的本質。那麼,為何中國的西進必須改變中國的本質呢?清朝建都北京,上承明朝,下開民國,中心在東而不在西,無可置疑,無論政、教、經、社、文等重大方面,都難以抹去漢化的烙印。清帝不僅以中國自稱,而且每年長時間居住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沒有漢化,何以今日滿族及其文化幾乎全部融入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與文化?漢化一如西化,並不隨任何人的主觀意願而存亡。
姚先生說“抵制全盤漢化當然不應該被等同於對漢化的全盤否定”,但何、羅辯論“漢化”所用的英文字都是“Sinicization”,從未有過“全盤漢化”(wholesale Sinicization)的提法。姚先生要為“新清史”辯護,加上一個“全盤”來曲解“漢化”,可謂用心良苦。請問乾隆有沒有“漢化”?當然有。請問乾隆有沒有“全盤漢化”?當然沒有。事實上,如何炳棣所說,漢化乃是一漫長過程,可追溯到史前;在這一過程中,多數所謂漢人也難免不染胡風,甚至有胡人的血統。換言之,在理論上,即使是漢人也不能說是“全盤漢化”。何炳棣當然也不是什麼“全盤漢化”論者,他認為中國一直是多民族的國家,很清楚地肯定滿族皇帝開拓疆域,建立了包括內亞在內的大帝國,以及增加人口與財富的偉大貢獻。姚先生沒懂得“何炳棣的做法”,就妄加指責,太不公平了。姚先生以“學術氣量和為人態度”責備別人,而硬將“漢化”拗成“全盤漢化”,是哪門子的學術態度?
清朝的“西進運動”
說到中國西進,可一提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國向西邁進:大清征服中亞記》(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書主要探討大清帝國之征討蒙古、新疆與西藏,以及與沙俄在綿長邊境上的對峙與交涉。他批評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將近現代中國的疆域視為當然,將內亞各民族統一於多民族的現代中國視為當然。他理解現代中國建立於被否定的過去並不特殊,也不願以善惡來定帝國的是非,並聯想十九世紀美國的“西進運動”(Westward Movement)。但他並未指出,現代美國疆域之建立也是以征服與殘殺為手段,而此運動也具有以“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許的強烈民族主義色彩,今日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這種發展趨勢不是濮培德所說“必然的”,不很“自然的”,那麼,將中國分為五塊、美國分為三塊才是正常的歷史發展嗎?
濮培德將清帝國、準噶爾(Zungharia)蒙古與俄羅斯帝國並列為中亞草原三要角,並不恰當,因三者本質有異,不可一概而論。姚先生將清代中國與沙俄羅曼諾夫王朝視為類似的舊式帝國,是不知“貌同心異”也。俄國的彼得大帝(1672-1725)與康熙大帝(1661-1723)約略同時,俄帝已全心全力西化,並親往西歐學習,俄國在其統治下,引進大量先進科技,補助新興工業以及執行“重商主義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整個十七世紀,愈來愈多來自西歐、中歐的商人、工匠、冒險家湧入俄國,追求商機與財富。不僅此也,連西歐的社會風俗也已進入俄國的上層社會。彼得大帝在其任內已使俄國成為歐洲強權之一。即使在彼得之前,俄國向東擴張也出於商機,俄皇伊凡四世(Ivan IV)以兵力支援巨賈Stroganov家族跨越烏拉山而東,輕而易舉地奪取了西伯利亞廣大的土地。俄國“殖民”西伯利亞的最主要目的仍是資源,特別是皮毛、貴重金屬以及容易取得的貿易品。將清帝國與俄帝國模擬,似是而實非也。姚先生認為俄國“具近代資本主義性質”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相當“冒失”的,因為到十九世紀,俄國與其他歐洲強權已從資本主義發展到所謂“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時期了。
從帝國的安全而言,沙俄之重心遠在歐洲,蒙古早已不構成威脅。然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退回草原後,仍然是明朝北疆的威脅,還需要修邊牆來防禦,至十五世紀蒙古領袖也先崛起,曾於土木堡大敗明師,並俘虜御駕親征的明英宗。北疆的蒙古威脅可說是與明朝相始終。清朝穩固了北疆,與漠西蒙古于太宗崇德二年(1637)建立朝貢關係,不再需要長城作為防禦設施;毋需再修築邊牆,但長期征討準噶爾也確有其安全的考慮。在十七世紀後半葉,出了強橫的雄主噶爾丹(Galdan)統合準噶爾成為內亞的一大政治實體。清廷平定準噶爾過程頗長,但卻不能如濮培德般以近代殖民帝國的眼光來看康雍乾三帝之擴張。濮書頗多扭曲,如謂康熙親征噶爾丹出師無名,噶爾丹也就成了康熙“擴張主義”的“犧牲品”。濮培德既知滿蒙關係密切(見濮書頁122、124、127),卻無視噶爾丹破壞滿蒙歷史關係之嚴重。康熙有言:“朕因是深知,此人(按即噶爾丹)力強志大,必將將窺伺中原,不至殞命不止。”(語見《平定朔漠方略御製記略》)
我們應該理解康熙刻意在北疆建立的安全秩序,而此一安全秩序則是建立在所謂“旗盟制度”之上。旗盟是一種各自管轄、不相統屬的制度,各旗之上雖有正副盟長,然盟長並不能干預各旗之內政,不過代表清廷監督而已,其目的顯然欲以自治來收安緝之效。所謂會盟,乃定期之集會,以便聯絡感情,解決問題,亦即康熙的柔遠之道,以蒙古為屏蕃,防備朔方,而其安全佈局之積極性與有效性遠勝於明代的邊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康熙長治久安的政策原本要與蒙古各族和平相處,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貢貿易來滿足蒙古族的物資需求,以資羈縻,與喀爾喀(Khalkhas)淵源尤深。喀爾喀有七旗三汗,于滿清入關前即已臣屬,建立了穩固的宗籓關係。康熙元年(1662)派遣理籓院尚書至庫倫會盟,宣達康熙諭旨,調解內部矛盾,諸汗一致遵從,大清帝國無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國。
然而康熙的佈局卻為噶爾丹所破壞,噶爾丹不斷向東掠奪侵吞,更介入西藏神權,又與俄國結盟,來鯨吞領地極為遼闊的喀爾喀蒙古,甚至還要煽動內蒙古。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甚而乘虛入侵內蒙古,劫掠殺戮,並造成大批難民。清廷聞報遣軍與喀爾喀兵與戰不利,更增其氣焰,乃乘勝南下,距北京城僅七百里,京師戒嚴。連京師重地都受到威脅,康熙實不得不於1690年7月27日宣佈御駕親征。不過,噶爾丹雖於烏蘭布通(Ulan Butong)之役受創,得以逃脫,但此役絕對是決定性的,噶爾丹此後一蹶不振,康熙更乘親征之便,親自與喀爾喀諸部會盟於內蒙古的多倫諾爾(Dolon Nor),重建安全秩序。但噶爾丹敗遁乞和之後不到兩年,又殺害清廷使臣馬迪,要求喀爾喀七旗脫離大清,再度向康熙的佈局挑戰。康熙遂不得不再度用兵,但展示軍威之餘,仍以招撫為主,所謂“宣化地方行圍”。由於噶爾丹未如期來降,康熙於1692年2月三度親征寧夏,率師出塞,昭莫多(Jao Modo)一役後,大批噶爾丹部眾歸服,青海諸部俱降。噶爾丹陷入困境,不久死亡。康熙親征剿噶爾丹歷時七年,代價固高,但使漠北喀爾喀蒙古更順服感恩,使喀爾喀蒙古得還故土,遂按內蒙古四十九旗之例,擴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統合。康熙晚年進軍拉薩,收服西藏,也是以維護邊疆固有的秩序,出發點是相當被動的。當準噶爾部於1718年之秋,入藏騷擾掠奪,並攻擊駐拉薩的七千清兵,擊斃清將鄂倫泰,康熙才命皇子胤褆率師入藏。
康雍乾三朝的邊疆政策有其一貫性,最後才能於乾隆朝徹底擊潰準噶爾,使沙漠南北、陝西、甘肅、青海、西藏等地區得享長期的安寧。這種政策與佈局顯然與濮培德所謂的近代殖民主義,以奪取資源、利用廉價勞工、開拓市場為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殖民的性質必須厘清,不可回避。姚先生不知“出於純粹防禦動機的擴張,是否就是一種應當予以肯定的擴張,或者是否至少比出於經濟動機的擴張擁有更多的正當性”?據我所知,大部分的美國人會說當然,至今美國仍憑其軍事優勢,為了其國家安全,在全世界擴張,不是嗎?既然姚先生也承認,“在清朝立場上看,準噶爾確實對它構成了重大威脅”,美國人應當理解,但濮培德並不理解,這就是不時出現的所謂雙重標準,不知姚先生是否懂得?
清帝國經營新疆,終於建省,應是新疆成為中國一部分的歷史過程,但濮培德不認為中國擁有新疆乃歷史之必然。我們要說的是,任何歷史結果或非必然,但結果不可能改變,濮氏曾提到美國之西進運動,加州或德州終於成為美利堅合眾國之一部分,雖未必是歷史之必然,亦不能改變“自然地”成為美國一州的歷史結果。姚先生以責備的語氣,說中國的讀者往往有思想上的障礙,即“錯誤地推導出如下的論斷,即自古以來就一成不變地存在著一個與今日中國版圖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絕不能變小的中國”。我不知道任何有水準的讀者會有這樣幼稚的推論,如他影射拙編作者,那便是姚先生自己的思想障礙了。更有障礙的是,姚先生以現代的國家觀念,視清與準噶爾為互不歸屬的國家。清朝要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才勉強接受近代國家觀念,在傳統中國,各政權是爭奪天下,不是近代概念上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否則三國爭雄豈不也成國際戰爭了?遼宋之間也是國際戰爭?姚先生如以為然,不妨改寫中國歷史。不過,無論古今中外,統一幾乎必須通過“兼併”來實現的,但姚先生似乎也有疑惑。
學者有無政治意圖?
“中國”這個名詞沒有姚先生說得那麼複雜,中國從來不是國號,而是泛稱或簡稱,早出現於先秦,隨著疆域的擴大,這個名詞所涵蓋的地區也隨之擴大。有一說,中國(China)即由Ch'in轉音而來,秦漢以降各朝代莫不以中國自居。大清自稱中國,則中國當然包括內亞在內的疆域。姚先生也知道“中國不等於漢”,但很多外國人不知道。我在美國住了四十年,深知美國人嘴上說的 “Chinese”指的就是漢人,因為他們認為“滿族”(Manchus)、“蒙古族”(Mongols)、“藏族”(Tibetans)、“維族”(Uygurs)不是 “Chinese”。有一年,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白人朋友從新疆訪問回來,他對我說:“那裏的人長得不像你”,也就是說那裏的人不是中國人。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是一女性黑人姓Rice,我回答說:“你們的國務卿長得跟你也不一樣。”美國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國家,卻不知道或不肯承認中國也是多民族國家。
“新清史”更提出“族群主權”(ethnic sovereignty)說,認為各民族有自己的認同,故有自己的主權,清國是滿人所建,所以不等於漢人的中國。記得“族群主權”的首倡者歐立德應《上海書評》訪談時,曾說他雖愛好漢文化,但他的國家認同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他的潛臺詞就是強調“族群主權”,滿人愛好漢文化,仍認同他們自己的族群。歐立德不想想清帝國內的漢族與滿族是認同兩個國家嗎?他自己即使接受中國文化,完全不影響他的國家認同是美國,乃兩碼事,可說引喻失義。他也沒有引用他的“族群主權”來主張美國的黑人或印第安人獨立建國。“新清史”將“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混為一談,拙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有詳細論述,請姚先生認真參閱。
姚先生讚賞他的老友甘德星在拙編中的文章《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認為“言簡意賅”。甘文以康熙皇帝為例,充分駁斥滿清皇帝不是中國皇帝之說。他用四份康熙遺詔,指出遺詔的重要性,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關鍵文書,顯示滿漢一體意識。康熙自稱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他所統治的都是“中國之人”。甘教授確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內亞。清帝設立理藩院處理邊疆事務,從滿文、蒙文、藏文對譯中發現都有“外”意,認為無疑視為邊地,“宜乎漢文稱之為藩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遺詔中,自稱繼承明朝的中國正統,並以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為榮。甘教授證明,滿清在康熙時,漢化已深,“滿漢已成一體,並同為中國之人”,結論是“新清史”所謂大清非中國之說,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國,其重心在關內漢地,康熙是以漢地為中心的中國之主,並非以中亞為軸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順治與之後的雍正、乾隆諸帝,亦複如此。姚先生既然認同甘文的論點,認為“意賅”,總不能如他所說“評論中的學術取向越強,批評就越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老友“心有餘而力不足”嗎?姚先生既承認康熙是中國的皇帝,“新清史”卻不這麼認為,豈能腳踏兩條船?姚先生的結論是“清朝和元朝不等於中國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這不就是拙編所要指出的新清史一大錯誤嗎?然則,姚先生為何認為我們因為“政治不正確”而批評新清史呢?更不可理解的是,姚先生悍然指責我們“滿眼只看見別人的‘謬誤’,把‘回應’變成一場聲勢兇猛的討伐式‘反駁’,對這種態度可能需要有所檢討”,姚先生此類主觀情緒性發洩毫無根據、不符事實,殊不宜見諸論學文字,這才是應該深切檢討的態度。
姚先生承認清朝不等於中國的說法是錯誤的,但又要曲說呂思勉先生不認為元朝是“中華帝國之延續”。呂先生把元朝寫在《白話本國史》裏,他的本國應該是中國吧,他寫的應該是中華帝國史吧,他寫的帝國史有中斷嗎?姚先生還要提“厓山之後無中國”的無聊之論,可見他雖同意他老友之說,仍心有未甘。其實,元、清不是“中華帝國之延續”,並非新見。日本的岡田英弘早就挑戰中華帝國元-明-清的序列,而認為是“元-北元與明的分裂-清”,清帝國自元取得正統性,再南下統一蒙元原來的領土,所以清帝國是蒙古國的繼承者。按此邏輯,清只能繼承元,中華民國就只能繼承漢人政權明朝了,也只能繼承明代的疆域了。這算“過度的猜疑”嗎?姚先生完全無感嗎?
“新清史”諸君都是學者,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政治意圖,美國學者對政治的影響也極為有限。但無可諱言的則是,這些所謂理論足以為具有政治目的者張目,質疑中國統治非漢人地區的政治正當性。這就是國內所謂“敏感”之所在。學術最好能避免政治,但往往難以避免。不料,姚先生卻祭出“政治正確”的帽子,說什麼評述新清史“往往隱含著對‘政治不正確’的高度,甚至過度猜疑”。姚先生似乎搞不清楚到底是政治不正確,還是史實不正確。新清史作者猜疑其批評者為“民族沙文主義”,並非實事求是討論問題,逾越了學術討論的分際。歐立德在其《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一書中傲慢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臺灣帶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限制了大部分學者去嘗試不同於刻板馬克思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Chauvinist)的滿洲史論述。”姚先生似乎認為這是振聾發聵之言,但在我們看來乃不實之言!老實說,我們在臺灣出這本書,未必“政治正確”,如姚先生指國內學者批評“新清史”,是因為“政治不正確”,須知姚先生的代言在彼邦絕對“政治正確”(此詞原是美國很通行的話)。我不認為姚先生言不由衷,而是沒真正懂得“新清史”的性質,也沒有好好閱讀拙編,憑一點不正確的印象就大發高論。
“新清史”並不“新”
事實上,所謂“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其核心議題並不很“新”,早在1920年代日本即有“滿蒙非中國”之論,很能配合日本當年的國家目標。十年之後就有“滿洲國”的成立;若非抗戰勝利,東北、內蒙古、臺灣豈能為中國所有?當歐立德提出“族群主權”的同時,所謂“疆獨”、“藏獨”、“台獨”,都已是當前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能說“過度猜疑”嗎?不過,中國應不應該這麼大,當然不取決於理論,而有賴於國家的實力,姚先生提到的“政治焦慮感”,以及嘴巴上的政治正不正確,根本無關宏旨。有趣的是,姚先生完全看不到“敵對勢力試圖分裂中國這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狼子野心”,還要責怪別人“脆弱多疑”。百餘年來至今,不少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圖”,難道姚先生真的一無所知嗎?當下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大家都知道針對中國,唯獨姚先生認為是“牧童遙指杏花村”。
姚先生在書評裏忽然評起鐘焓的文章,雖與拙編無關,但他說鐘文不夠全面,我覺得姚先生不僅對新清史的認識不夠全面,對何炳棣的認識更不夠全面。他說“新清史”對利用滿文確有宣導之功,利用滿文史料是新清史宣導的嗎?非也!早有學者利用滿文史料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大學歷史系就有廣祿教讀滿文,也培養了一批能用滿文治清史的學者如陳捷先、黃培、莊吉發、甘德星等人。我不知大陸的情況,必定也有。據精通滿文的朋友告知,新清史諸君的滿文程度相當有限,遠不如他們有限的漢文程度。滿文史料當然重要,我們更期盼能就滿文史料寫出重大的翻案文章,可惜至今尚未出現。史料絕不嫌多,充分利用滿文、蒙文、藏文等史料,求之不得,但有人認為漢文史料只能揭示漢人眼中的清帝國,這就有點奇怪了,難道清代大量漢文文獻看不到滿人的觀點?很多清政府的政令都是由漢文發佈的,不是嗎?
姚先生以“從事學術批評時,針砭尺度宜縮不宜增,絲毫不可效尤過去政治大批判中盛行的那種肆意拔高、無限上綱的作風”來評論拙編,將學術討論與政治批判混為一談,對我們來說,不僅荒謬,而且有點可笑。姚先生不知在國外學術論辯,往往是不留情面的,是有增無縮的。姚先生既然認為“新清史研究中當然還有很多值得再討論的問題或者錯誤”,卻以為我們提出討論與指出錯誤是不應該的,也不認真討論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所指出的錯誤,而以教訓式的口吻,要我們的“心態調整得更理性一些”。沒想到姚先生居然如此高傲,真有點匪夷所思。
最後姚先生提到韓儒林教授。我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學與他有一夕之談,得知他于戰後曾赴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後因怕白色恐怖又回到大陸,並談及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他是一位謙謙君子,有名的元史專家,絕不會認為元朝不是中國的朝代。姚先生所引韓教授的話,如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和文化,誰會說不是?說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只我們中國人自己在研究,誰又會說不是?事實上,近百餘年,日本及歐美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者,不知凡幾。二戰後,美國研究中國更進入學院化,對中國近現代史尤其重視,作品可稱汗牛充棟。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老是覺得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連研究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也不如人。現在姚先生對我們批評新清史很不以為然,並一再重複政治正不正確,我們應講究的是史實正不正確。寫書評要先讀懂內文,要注意批評得正不正確、公不公平,願與姚先生共勉。(2015年4月27日寫於臺灣新北市大未來居)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17日
延伸閱讀:新清史理論之盲點:大清即中國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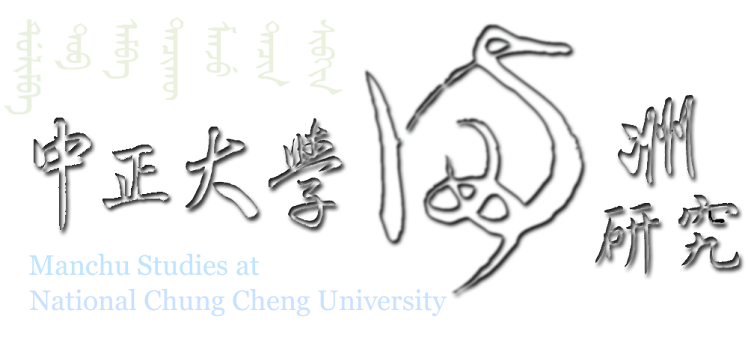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